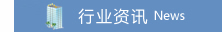
| 推動第三方治理有幾重深意? |
| 2015-1-23 12:17:19 閱讀次數:898 |
2015年是國家“十二五”規劃的收官之年,也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提生態文明制度建設改革目標的第三個年頭。無論是從完成“十二五”規劃節能減排的目標任務來看,還是從加快和深化全面改革的進程來說,今年都是非常關鍵的年份。尤其是如何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推進全社會的生態環境保護,如何利用市場經濟的規律和規則提高各部門對環境資源的配置效率等,這些顯然都將成為2015年生態文明建設的重中之重。 就在1月14日,國務院辦公廳正式印發《關于推行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雖然《意見》僅僅針對的是“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這一主題,但是實際上這個由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意見》卻承載著非常重要的使命。那就是,在前期落實和推進各項環境法律法規和政策的基礎上,我們開始嘗試從最為關鍵的環節出發,開展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與生態文明建設相結合的有益探索。可以說,這既是一種嘗試和探索,更是一場攻堅戰。 筆者認為,對于上述《意見》,要著重理解其中的4個關鍵問題。 第一,環境治理中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在環境污染的源頭上,目前比較一致的看法是,市場失靈造成了過度生產,進而引發了過量的污染排放。因此,如果要從源頭減少污染排放,那么顯然需要政府的介入,譬如采用征收環境稅、開展排污權交易等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這樣的邏輯也曾被用來理解環境污染治理,也就是污染物被排放出來后,需要政府強力干預才能加以凈化處理,生產出社會所需的環境公共產品。在此,如果將環境污染治理過程僅僅理解為生產標準的公共產品,那么政府顯然無法置身事外,理應直接參與其中。但事實上,在目前大多數的環境污染案例中,我們都可以在環境質量與環境污染之間找到直接的因果關系或證據。 這意味著,即便環境治理的結果是公共產品,我們也可以找到相對應的治理主體,那就是排污者自身,要求他來付費。這個特性將環境治理與其他一般性的公共產品區別開來,進而為市場的介入創造了可能。 也就是說,實施“誰污染,誰治理”原則的基石本來就是市場,而不是政府干預。政府在此所需要做的,就是通過法律來確定這條原則,而不是直接介入到環境治理的具體過程中。 第二,環境治理中需求與供給的關系。如上所述,市場是環境污染治理的基石。那么接下來的問題是,誰是污染治理市場的需求者,誰又是這個市場的供給方?在以往環境污染治理的過程中,由于角色不明朗,一方面,政府往往以污染治理市場的主要需求方出現,也就是通過政府采購的方式來發出需求信號。另一方面,排放污染物的企業在上繳排污費之后,往往自認為無需再對環境改善擔負責任,即便是在非法排污之后,也因為違法成本低而寧可繳納罰款,卻不主動治理。這樣的結果是,相對于環境質量改善而言,需求意愿不足,從而無法推動創造出真正的供給。 對此,其實完全可以改變思維,基于上述“誰污染,誰治理”的原則,政府應該轉變自身角色,減少直接購買,轉而盡最大可能地將污染方推向市場,使其成為治理市場上的需求主體。這一點也正是本次《意見》的主要理念之一。當然,要實現這一點,就必須在源頭上堵住排污與處罰之間的模糊空間。同時,要給排污企業一定空間,讓其自行選擇治理污染的方式,或者自行治理,或者購買市場上的環境服務。只有理順需求與供給之間的關系,才能真正推動和發展污染治理市場。 第三,環境治理中產業與資本的關系。在有了充足的需求后,就給市場的供給創造了可能性,也就是為環境服務產業的大發展奠定了基礎。不過,事情顯然并沒有這么簡單。 根據之前合同能源服務市場發展的情況,即便是企業有了這樣或那樣的節能減排需求,結果卻發現市場上甚少有符合資質或能力要求的服務類企業。這是為什么?這并不是由技術、人才等方面的瓶頸造成的,而是由于資本的緣故。一方面,在節能減排上有需求的企業,沒有額外的資金投入到設備、設施的大規模改造中;另一方面,提供節能減排服務的企業大都規模較小,也無法籌措到足夠的資金,進而一度造成了有價無市的局面。 對此,筆者認為,要為環境服務類企業營造充分的市場空間,就必須對其給予一定的培育,發揮出資本市場的放大效應。對于這一點,《意見》未雨綢繆,充分考慮到了資本市場在推動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中的作用,提出了價格、財稅、金融和引入社會資本等幾個層面來引導和支持環境服務類企業發展的建議。 第四,旨在推動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環境服務業與經濟發展的緊密聯系。放在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這一問題的核心之處在于,一是如何將生態環境保護的需要與國民經濟的結構轉型相結合;二是如何將生態環境保護的治理過程與國民經濟發展模式和形態轉變相結合。 上述兩點歸納起來,也就是說,在經濟增速下滑、結構出現調整之際,我們既要加大保護生態環境的力度,同時更要從發展的視角出發,將生態環境保護的治理過程轉化為國民經濟增長的動力和潛力。由此,推動環境服務業健康、有序、科學發展,無異于同時作用于環保和經濟兩個層面。這,也許正是《意見》出臺的最根本之處。 |